拉康 / “享乐” → 快乐、高潮、欲望、伦理学、大他者、女性、身体、语言
(本文同时发于我们的微信号拜德雅Paideia)

大家好,拜德雅图书工作室2021年年度重磅新书之一《拉康精神分析介绍性辞典》(迪伦·埃文斯 著,李新雨 译)现已入库,目前正在打包快递(由我们此书合作的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直接寄出)。此次订单量较大,发货所需时间也会长一点,我们会全力在6月内都发出,望理解。再次,拜德雅图书工作室全体成员向大家致以感恩的心。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订购,识别下图中二维码即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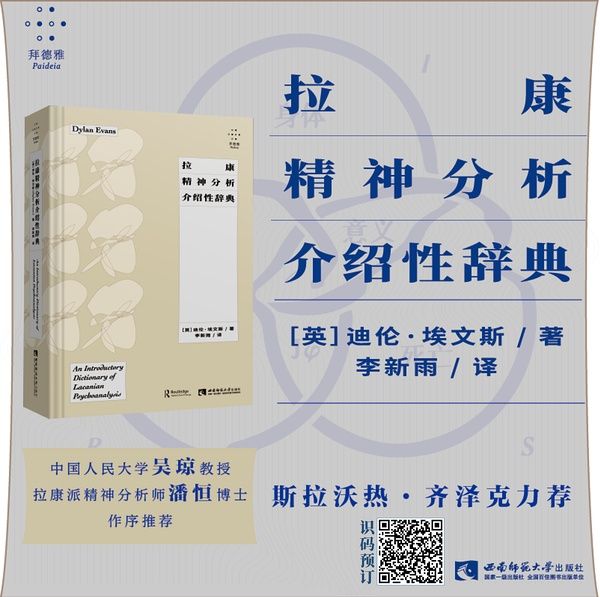
识码预订
《拉康精神分析介绍性辞典》译者李新雨特别翻译了本书作者迪伦·埃文斯早期的一篇长文:《从康德式伦理学到神秘主义经验:拉康式“享乐”探究》(From Kantian Ethics to Mystical Experience: An Exploration of Jouissance, in Key Concepts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 Dany Nobus ed., New York: Other Press, 1999, pp.1-28)。这篇长文我们拟分四次推送(欢迎关注话题专辑“拉康式‘享乐’探究”)。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该文的第二部分(特别说明:【】为注释编码,注释会在第四次跟第一部分[引言]和第五部分[结论]一起推送)。
II.享乐在拉康著作中的多重色调
鉴于“享乐”概念在拉康后期著作中逐渐获得的重要性,或许非常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术语完全没有出现在其早期的著作之中。在拉康的战前著作中丝毫没有对它的提及,而事实上,直至拉康在1953至1954年举办的第一期公开研讨班,这一术语才首度出现。【5】即便在当时,这一术语也只是偶尔出现,直至1958年它才开始在拉康的理论词汇中扮演起一个重要的角色。从那时起,“享乐”便呈现出了一种愈来愈大的重要性,直至1970年它才变成了对于拉康思想而言的一个关键性概念,以致于如果我们要挑选出最具重要性的拉康概念的话,那么“享乐”与“对象a”便将是唯一的争夺者。
在这一术语突显出来的过程之中,“享乐”一词并未获得一个稳定的意义。恰恰相反,正如绝大多数拉康的术语那样,它的回响与道说皆随着拉康教学的过程而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转变。考察这些转变的一种方式,便是要将它们解读作一个单一概念的渐进性展开;这也是奈斯托•布劳恩斯坦(Nestor Braunstein)在其有关这一主题的说明性论著中呈现“享乐”的方式。【6】然而,这样的一种取径却格外不一致于拉康自己的阐述风格,拉康的风格从不旨在给每一术语制作出某种具有一致性的单一的意义,而是相反旨在发展出一些相互间往往是不一致的不同的意义。因此,在下文中,我将简单地概述“享乐”概念在拉康文本中的不同位点上所出现的那些不同的细微差异,而不会试图以某种主人式的“综合”来调停它们。这并不是说这样的综合就一定是错误的,因为拉康教学的一大魅力便在于它会邀请读者为其自身去建构出这样的一些综合。显而易见的是,当拉康的评论者建构出某种综合的时候,他便必须要注意将此种综合的解释性本质置入前景,因为否则的话我们便会犯下某种风险,正如布劳恩斯坦所做的那样,亦即把某种特殊的解读呈现作是内在于文本自身之中东西。在选择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来探讨享乐的同时,我希望能够将这一综合的任务交付给读者来裁决,同时我也会提供一些根据来批判由此产生的这些综合。
1.享乐之为快乐
在拉康之前,“享乐”一词并未出现在精神分析的术语学装置之中。最接近的德文同义词“Genuß”(享受)既没有构成弗洛伊德的理论词汇的一部分,也没有让任何法国精神分析家给这一术语赋予任何特殊的价值。拉康似乎是根据某种哲学上的传统而将这一术语引进了精神分析——亦即:经由亚历山大•科耶夫(Alexandre Kojeve)所发展起来的黑格尔哲学传统,拉康曾在1930年代参加过科耶夫关于黑格尔的讲座。拉康自己就将“享乐”这一术语归于黑格尔,但是这样的一则评论却必须受到一个事实的限定,亦即:每当拉康提及黑格尔的时候,他在脑海中想到的始终都是科耶夫的黑格尔。【7】因而是科耶夫而非黑格尔本人,在主奴辩证中首次强调了“享乐”的维度:
〔主人〕同样可以迫使奴隶为了他去“劳作”,以便将其“行动”的果实出让给他。因而,主人便不再需要作出任何的努力来满足其自身的(自然性)欲望……至此,在自然中保存其自身而不参与同自然的搏斗,便是在“享受”(Genuß)中生活。主人在丝毫不作出任何努力的情况下便获得的这种“享受”,便是“快乐”(Lust)。【8】
当“享乐”这一术语在1953至1954年的研讨班上首度出现于拉康著作中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科耶夫对于拉康的影响。在此,这一术语被专门用于讨论主奴辩证的语境,而且它似乎也指代的无非是某种形式的“快乐”。因而,当主人迫使奴隶去劳作的时候,奴隶便会生产出只有主人能够对其占有并享乐的对象:
实际上,从〔由主人与奴隶构成的〕这一神话性情境开始,某种行动便被承担了起来,从而在“快乐”〔享乐〕与“劳作”之间建立了某种关系。主人将某种法则强加在奴隶身上,亦即他必须去满足他者〔亦即主人〕的欲望与快乐(享乐)。【9】
因而,奴隶就变成了强迫型神经症患者的范例,强迫症患者已经死了,这并非是对他自己来说的,而是对他的主人来说的,因为强迫型神经症患者业已抹除了其自身的享乐。【10】由于放弃了他自身的享乐,强迫型神经症患者便会将它转嫁到一个想象性的小他者身上,于是他便可以用笼中困兽的那些嫉妒性眼光来看待主人的享乐。【11】
2.享乐之为高潮
如果说拉康在其1953至1954年与1954至1955年的两期研讨班上最早对于这一术语的使用缺乏了享乐的那些性的意涵,那么这些意涵在几年之后则变得相当明显起来,当时拉康使用这一术语来指涉“手淫”的快乐。【12】就拉康对于该术语的使用而言,这一指涉即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在此之后,“享乐”便明显总是由性欲的维度来标记的,即便在一开始,这里的“性欲”尚且还带有某种明显的生物学论点。换句话说,“享乐”被简单地等同于“高潮”的感官愉悦,因而仍然被定位在“需要”和生物性满足的辖域之中。例如,在1958年关于“女性性欲”的一篇文章里,拉康便将“性冷淡”说成是某种“阴蒂享乐”的缺失。【13】这一论点必须连带着他在同一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一起来阅读,“性冷淡”在其中被定义作“在专属于性欲需要的满足上的缺失”。【14】即便在很久之后,当“享乐”的概念在拉康的著作中远远超出了与性高潮的等同而呈现出多重意涵的时候,这一层面也从未遭到全然的抛弃。因而,拉康便可以在1963年将“享乐”简单地注解作“高潮”,并且在他1973年关于贝尔尼尼(Bernini)的圣特雷莎修女的雕像的评论中公然地玩味这一意义。【15】
如果说拉康在1953至1955年对于“享乐”这一术语的首度使用是受到了科耶夫的启发,那么他在1956年之后转向这一术语的性的意涵则很可能是受到了乔治•巴塔耶著作的启发。拉康自己并不承认这一债务;事实上,在整部《著作集》中仅有一处对于巴塔耶的直接参照,而在《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中也仅有一次提到了巴塔耶的名字,在这期研讨班中,拉康对于萨德的讨论可能也具有着更高的价值。【16】然而,正如弗朗索瓦•佩里耶(François Perrier)与大卫•梅西(David Macey)所指出的那样,在拉康后期于“享乐”的概念化之中,存在有很多迹象都表明他受到了巴塔耶的影响。【17】不仅是“享乐”的致死性特征会非常强烈地令人联想到巴塔耶把“爱欲”看作是与“死亡”本身相接壤的暴力领域的观点,而且巴塔耶也同样把爱欲的“欢愉”(joie)刻画作某种必然性“过剩”的特征,并将其比较于不可言喻的神秘主义经验(正如拉康所做的那样)。【18】再者,巴塔耶也还预期了拉康有关享乐的悖论性特征的评论,他曾经写道:“我们在没有太多焦虑的情况下忍受它的同时,也应当享乐(jouir)于这种遭受丧失或是遭受危险的感觉”。【19】对于巴塔耶而言,这一悖论乃起因于性高潮本身的性质,后者总是以一种死亡般的颤栗而告终。
3.享乐之于欲望
在1958年之前,拉康对于“享乐”这一术语的偶然使用,似乎也符合于该词的惯常用法;它是“快乐”的同义词,特别是那种剧烈的肉体性快乐,对此的范例便是性高潮的快乐。然而,从1958年开始,这一术语却逐渐获得了一种全新的特别拉康式的意义。这一全新的意义是从拉康所发展的那些区分之中显露出来的,亦即:“享乐”与“欲望”之间的区分,以及“享乐”与“快乐”之间的区分。
“享乐”与“欲望”之间的区分是在拉康关于“无意识的构型”的研讨班中被首度发展出来的,尤其可见于1958年3月的那几场讲座。【20】在该期研讨班中,拉康声称在这两个术语之间作出一种细致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关于他自己如何理解这一区分,他却仅仅提供了一些很少的线索。在这一问题上,拉康最为清晰的说明出现在其1958年3月26日的讲座上,当时他宣称道:“主体并非是单纯地满足某种欲望,他享乐(jouit)于欲望,而这便是其享乐的一个基本的维度。”【21】换句话说,欲望并非是一种朝向某个对象的运动,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它便只是会单纯地去满足这一欲望。恰恰相反,欲望缺乏能够满足它的对象,且因此必须被构想作一种无限追寻下去的运动,而这则仅仅是为了对其进行追寻的享乐(jouissance)。因而,享乐便脱胎自某种生物性需要的满足的辖域,但却反而变成了一种悖论性的满足,而只能在追寻一种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欲望中之被发现。故而,丝毫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拉康立刻便将“享乐”联系于“受虐狂”的现象。
关于享乐与欲望之间关系的这些最初的评论,皆意味着享乐是维持着欲望的东西,因为正是对于欲望的享乐为了欲望的缘故而在满足的缺位中保持着我们的欲望。然而,欲望与享乐之间的关系在后来却被拉康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了出来。例如,在其关于“焦虑”的研讨班中,拉康便声称说“欲望会将其自身呈现作一种享乐的意志”,而这则似乎是把享乐安置为欲望的终点,亦即欲望所指向的目标。【22】我们现在的问题便在于要解释为什么欲望永远都不会抵达它所寻求的那种享乐,也在于要解释为什么享乐的意志永远都是“会遭遇到其自身界限与其自身限制的一种失败的意志”。【23】
这里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关于享乐与欲望之间关系的此两种说明之间的差异。在第一种说明中,此两者是共同存在的:如果主体享乐于欲望,那么享乐便维持着欲望。在第二种说明中,如果说欲望以享乐作为其自身的目标,那么欲望的基础则在于某种享乐的缺失,因为我们只能够去欲望我们所没有的东西。在拉康的后期著作中,居于主导的正是这后一种说明。
4.享乐之为一种根本性的伦理学立场
如果说拉康在1958年开始发展出来的“享乐”与“欲望”之间的区分构成了这一术语的第一个特别拉康式的轴向,那么“享乐“与“快乐”之间的区分则构成了第二个特别拉康式的轴向。在1960年,拉康在其研讨班《精神分析的伦理学》的语境下发展出了这一对立。【24】在这里,享乐不再被单纯地等同于快乐的感觉,而是渐渐开始指代相反的感觉,也即身体性或心理性痛苦的感觉。这并不是要把享乐等同于受虐狂,因为这里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差异。在受虐狂中,痛苦是一种获得快乐的手段;快乐恰恰得自于使自身遭受痛苦的事实,以致于我们在受虐狂中很难将快乐与痛苦区别开来。但另一方面,就享乐而言,快乐与痛苦则始终都是有所区别的;没有任何的快乐会得自于痛苦本身,而且在没有付出痛苦的代价的情况下也无法获得任何的快乐。因而,享乐便是一种“交易”,在其中“快乐与痛苦被呈现作一个单一的封包”。【25】拉康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里借用了一个例子来阐明这一观点:一个男人有机会与其魂牵梦绕的那个女人云雨一番,但却被告知说倘若他这么干了,他便会在完事之后被送上断头台。【26】
“享乐”(在这一更新的意义上来理解)与“快乐”之间的此种对立也同样涉及到了对于后一术语的更新的理解。现在,“快乐”便一方面指代着“快乐感官”,而另一方面则指代着“快乐原则”。“快乐原则”是弗洛伊德在其元心理学著作中所讨论的“精神运作的两大原则”之一(另一项原则是“现实原则”)。【27】它是主体在“趋乐避苦”的基础上来支配其自身行动的先天倾向。至此,我们便应当可以相当明显的看到,虽然在前一种意义上的快乐同义于享乐的较早前意义,但是在后一种意义上的快乐则实际上对立于享乐的较晚近意义。如果说康德例子中的那个男人受到了快乐原则的支配,那么他便不会仅仅为了跟其梦中情人短暂地云雨一番而付出死亡的代价。快乐原则会涉及到某种“代价—收益”分析,正是这一点使这个男人拒绝了享乐的交易。或者用拉康的话来说:“正是快乐安置了一些对于享乐的限制。”【28】
然而,精神分析的功绩却恰恰在于它指出了存在着某种“超越快乐原则”的东西。【29】换句话说,并非所有的人类决定都会受到“理性”的计算所支配,在这样的计算中,人们会权衡潜在快乐与潜在痛苦之间的利弊。但也确实存在有一些人会为了与他们的梦中情人共度春宵而付出了死亡的代价。因此,享乐的交易也并非总是会遭到拒绝。
康德用这个面对着为了性欲而付出死亡代价的选择的男人的例子来说明“假言律令”,后者先于他对真正伦理学决定的讨论。如果这个男人出于自私的“病理性”考虑而选择放弃了这场交易——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男人不是基于“道德法则”来作出决定,而是基于权衡他在快乐中的获益并规避他要为此而付出的代价来作出决定的话——那么这便不是一种根本性的伦理学立场。只有当某种行动忽视掉在潜在快乐与潜在痛苦之间进行权衡的正常计算,这样的行动才能够称得上是伦理性的行动。如果我们将这一点转换至拉康在快乐原则与享乐之间所作出的区分,那么快乐原则便将对应于康德式的关于快乐和痛苦的病理性计算,而“鉴于享乐恰恰意味着对于死亡的接受”,享乐则会被定位在伦理性的一边。【30】
通过根据康德式的伦理学而将快乐与享乐区分开来,拉康也同样澄清了“死亡冲动”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允许了一个人可以不顾及权衡快乐与痛苦的正常“理性”计算,并因而变得能够作出一个真正的伦理性行动呢?难道这不恰恰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事实吗?亦即:快乐原则并不拥有着普遍性的影响。换句话说,拉康的观点即在于,恰恰是“超越”快乐原则的死亡冲动的存在使得伦理学的地带成为了可能。
5.大他者的享乐
在上一小节中,我们已经看到享乐的意义如何在1960年发生了转变,亦即从简单地等同于快乐而转向了快乐与痛苦“在一个单独的封包里”呈现出来的交易。然而,正如绝大多数拉康的术语学创新与概念性转变一样,享乐的较新近意义并未简单地取代享乐的较早前意义;相反,此两种意义是共同存在的。故而,在1960年之后,我们便可以发现在享乐的较古老意义(享乐是快乐的同义词)与享乐的较新近意义(享乐是快乐与痛苦的“封包”)之间存在着某种摆荡。因而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始终能够发觉在拉康使用这一术语的任何特定地点上到底是哪一种意义在起作用。冒着某种过度简单化的风险,我们可以在这里指出:在1960年之后,当拉康谈到主体的享乐,与之相关的是较新近的意义,而他对于大他者的享乐的讨论则会唤起将享乐等同于快乐的较古老的意义。换句话说,大他者的享乐并不是由刻画了主体的享乐之特征的那种痛苦性元素来标记的。
拉康在一种常见的临床现象上所作出的那些评论也证实了这样的解读,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幻象,亦即:别人“并不会像我这样被搞得一塌糊涂”,别人的家庭也不会遭到破坏掉我自己家庭的那些黑暗的力量所侵扰,那些没有症状的主体都是全然快乐的,他们不会提出这么多问题,他们会在自己的床上酣然入睡。拉康将此种“幻景”称作是只有大他者才能触及的享乐,而这似乎也同样证实了这样的一种观点,亦即:当联系于大他者的时候,享乐便会折返至先前与快乐的等同而失去其痛苦的意涵。【31】
这种只能归于大他者的过剩享乐的幻象的起源明显可见于儿童的早期经验,当时作为原初大他者的母亲可能在孩子看来是完整的、自足的,而且她对自己的快乐也是独立于孩子的。因为这个完整的大他者没有给孩子留出任何空间,所以孩子便会试图在大他者的身上写入某种缺失,例如,孩子会试图在母亲那里引入某种焦虑的音符,这或许是通过哭闹,要么就是通过拒绝进食。如果这一切都没有成功(也就是说,如果孩子的哭闹丝毫都没有扰乱母亲的享乐),那么孩子便无法制作出其自身的欲望;欲望与享乐在这里是明显对立的。然而,如果孩子成功地扰乱了母亲的享乐,那么这便会向孩子证明大他者是不完整的,亦即母亲的享乐并非是丰盈的。可是即便如此,孩子对于母亲的完整享乐的最初印象的记忆也会持续存在于这样的一种幻象,亦即:只有大他者才能触及那种丰盈的享乐。
6.女性的享乐
上一小节中的那些评论皆意味着,相信大他者的享乐在某种意义上比我们自己的享乐更加完整的这种信念纯粹是一种幻象。然而,在拉康的教学中,还是有那么一些时刻暗示出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实际上,的确存在着一个大他者,其享乐是更加巨大的。这些暗示都呈现在当大他者被等同于“大写异性”或“他者性别”的时候,对于拉康而言,这个绝对异性的“他者性别”总是女人。这一思想首先出现在他有关“焦虑”的研讨班上,当时拉康(借提瑞西埃斯的名义)声称:“是女人们在享乐。她们的享乐要大得多。”【32】
女性的享乐在某种程度上要大于男性的享乐,虽然拉康的这一观念在1963年还是全新的思想,但是将享乐联系于“女性性欲”则不然。早在1958年,拉康在其有关“女性性欲”的讨论中就已然使用到了“享乐”一词,它标志着那种可能会变成一种“持续性交合”的体验。【33】实际上,除了在探讨女性性欲的语境之外,拉康在任何语境下都从未如此频繁地使用到“享乐”这一术语。正是这一点致使一些评论家观察到:拉康对于“女性特质”的讨论往往是一个重要的移置的地点:在此种移置中,女性性欲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关于女性享乐的问题。【34】
在这一语境下,享乐要被理解作对于某种形式的性欲满足的实现,而且往往(但并非总是)等同于高潮。因而,男性享乐与女性享乐之间的区分便依赖于这样的一则假定,亦即:对于男人们和女人们来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性欲满足的形式。起初,这一区分仅仅被拉康呈现为一个程度的问题,正如在上述的评论中那样,女性的享乐要远远大于男性的享乐。因此,这一区分便并未触及到享乐本身的性质,拉康曾经认为享乐的性质是阳具性的:“享乐——就其是性欲化的享乐而言——是阳具性的享乐,而这即意味着它并不联系于大他者本身。”【35】然而,拉康在后来却又提出了一种不同“形式”的享乐,一种“超越阳具”的特别女性化的享乐。【36】尽管拉康早在其1958年关于女性性欲的文章里就已然谈到了女性享乐的问题,但是这却仅仅是对立于“阴道享乐”而非对立于“男性享乐”的“阴蒂享乐”。【37】鉴于弗洛伊德在阴蒂与阴茎之间制作的等同,这一对于女性享乐的早期指涉便无法被解读作是指明了一种在性质上有所不同的享乐形式,而是仅仅涉及到女性对于两性皆有的阳具形式的享乐的体验。然而,在1972至1973年的研讨班上,拉康确实又将女性享乐说成是一种在性质上有所不同的形式。阳具享乐继续是由两性共同体验到的某种普遍性的东西,但是除了此种阳具享乐之外,女人们却可以抵达另一种形式的享乐。【38】与阳具享乐不同,这一“补充性享乐”确实联系着大他者本身。但是除此之外,关于它却只有很少的东西可说。关于这种享乐形式的性质,拉康自己就没有提供太多的说法:实际上,他就曾指出我们不可能去道说此种享乐,因为此种享乐的经验并不会通往任何关于它的知识。【39】女性享乐的这种不可言说的本质,导致拉康根据神秘主义的经验来对其进行刻画,而不可言说性则始终都是神秘主义经验的特征之一。他在其讨论中指出的形象,便是贝尔尼尼的圣特蕾莎修女快要被天使的金色长矛所刺穿的形象。正如圣特蕾莎修女自己对于这一事件的描述所清晰表明的那样,这一神秘主义的“狂喜”的时刻强烈地暗示出了性高潮的享乐,拉康在《研讨班XX:再来一次》中也评论道:我们只要看一看这尊雕像,便会意识到圣特蕾莎修女正处在高潮之中。【40】
7.身体的享乐
因为在拉康的话语中,大他者不仅指代着“他者性别”,而且也指代着“身体”,所以几乎不会令人惊讶的是,拉康不仅将大他者的享乐联系于女性特质,而且也将其联系于身体。事实上,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拉康首度引入一种“超越阳具”的享乐的概念时,他便立刻将其指认作“身体的享乐”。【41】这一身体的享乐被更进一步地描述作“实体”,拉康在使用“实体”一词时完全清楚其全部的哲学回响。他指出,享乐是精神分析唯一认识到的“实体”。【42】如同弗洛伊德的“力比多”概念一样——拉康将其联系于身体的享乐——这一实体往往也会根据那些水力学的隐喻来描述。【43】因而,它便可以被描述作在主体诞生时被贯注到身体上的某种“流体”,其中的一部分必须要被“排干”,以便实现“文明化的工作”(弗洛伊德)并允许主体对于象征界的进入(拉康)。换句话说,阉割便可以被理论化作放弃掉我们从中诞生出来的那一部分身体的享乐:“阉割即意味着享乐(jouissance)必须被拒绝,以便它能够在欲望法则的翻转阶梯(l'echelle renversee)上被抵达。”【44】
拉康对于阉割情结的此种说明吸收了遍布在弗洛伊德著作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贯穿于弗洛伊德的著作,我们都会发现这样的一种思想:为了进入社会,主体必须放弃掉某种事物。这个主体必须放弃掉的“某种事物”以不同的方式被描述作“全能感”或是“本能满足的一部分”。【45】在社会秩序中占据某种位置的条件,便在于个体借以被诞生出来的那部分本能生活的原始配额必须永远地丧失。这一部分的享乐配额是“不可用”的;它不会在社会中实现任何有用的目的,且因此必须根除出去:
一般地讲,我们的文明是在压制本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每一个体都要交付出其拥有物的一部分,而个体必须放弃掉的那部分本能的满足便会作为某种牺牲而被献祭给上帝。【46】
正如弗洛伊德式的“本能满足的部分”一样,拉康式的享乐也是必须被牺牲掉的一种不可用的剩余。然而,在拉康对于“牺牲”的讨论中,他却针对内隐于弗洛伊德说明中的功利主义的社会模式进行了批判。拉康认为,牺牲掉本能满足的一部分,并不会简单地导致对它的消灭。恰恰相反,被牺牲掉的享乐会在“超我”之中聚集起来,并由此以“恶”的形式而返回。弗洛伊德谈到的“上帝”因而便不能被设想作一个仁慈的上帝,甚至也不能被设想作斯宾诺莎的那种静怡而超然的上帝,而是首先要被构想作一个“黑暗的上帝”。【47】
因而便不存在任何卫生学的方式来消除作为有用性需要之剩余的这一过剩的身体享乐。尽管“享乐是无用的”,正如拉康所宣称的那样,然而它却无法被简单地处理掉。【48】“剩余”往往是拉康故意使用的术语,因为在1960年代末左右,拉康自己便继续将享乐联系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进而创造出了“剩余享乐”(plus-de-jouir)这一术语。【49】剩余享乐的概念指的是:在阉割从身体中排出了享乐之后,仍然总是会存在有一定量的剩余。【50】这一享乐的剩余因而便会被捕获在身体的碎片之中,例如在构成“爱欲源区”的身体边缘,或是在癔症症状的内核之中。
8.享乐与语言
享乐被捕获在症状之中,这种说法也标志着拉康话语中的另一项重要的转变,亦即:从症状作为一种语言现象,转向不再能够被完全化约至语言的某种东西。拉康在1960年代早期便开始转向了这一观点,正如他在其1963年的评论中所清楚表明的那样,与行动搬演不同,症状并不要求解释,因为就其本身而言,症状并非是一种朝向大他者的呼唤,而是不指向任何人的一种纯粹的享乐。【51】但是,直至1970年代,这一转向才以“圣状”的概念而变得完全清晰起来。【52】尽管拉康曾在1950年代将症状看作是一种要进行破译与分解的信息,然而“圣状”一词则指代着一种“超越分析”的能指化构型,它是免疫于象征界效力的一种享乐的内核。因而,这便不再简单地是“它在言说”(ça parle)的情况;现在我们也同样有必要宣称“它在享乐”(ça jouit)。【53】这后一种观点也反映了弗洛伊德对于“阻抗”的发现;换句话说,在经过解释之后,还仍然存在着某种超越象征化并因而抵制分析家的语言性干预的一种享乐的元素。
拉康思想中的这一发展虽然回答了一个问题,但却仅仅是为了提出另一个问题。它所回答的问题关系到人们针对拉康的著作所提出的一个主要的批评,亦即:拉康把一切都化约至语言。但在发展享乐概念的时候,拉康则指出了一种超越语言的强大力量,从而驳斥了这样的一种批评。不过,这却又创造出了另一个理论性的困难,亦即:语言与享乐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如果说享乐纯粹是超越语言的,那么鉴于分析家唯一的工具便是语言的工具,他又如何能够在分析者的症状上获得某种效力呢?
这一问题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回答。一方面,我们可以指出,享乐借以从身体中被排空出去的阉割的运作,首先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的运作。正是那些强加的规则与禁止在阉割情结中将享乐的原始配额排除出了孩子的身体,而分析家也会在精神分析的进程中通过强加一些其他的规则来延伸这一阉割的过程。然而,这却仍然没有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亦即:那种无法受到解释的症状的元素亦或那种无法排空出去的享乐的内核究竟与什么有关?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用“圣状”来做些什么?拉康的回答是:分析可以将主体带向对于“圣状”的认同,也就是说,分析可以让主体认识到:“圣状”非但不会要求通过某种分析性的消解而把主体变成某种无症状的存在,与此相反,“圣状”的病理性标记恰恰是通过给主体提供对于其享乐的独特组织而能够“允许主体活下去”的东西。
另一方面,拉康也同样进一步质疑了他在其早期著作中所提出的语言与享乐之间的简单对立,同时他还更进一步指出:能指本身即是享乐的原因。【54】语言(langage)作为能指网络,可能会经由排除享乐而运作,但是这也掩盖了一个事实:语言(langage)是由“呀呀儿语”(lalangue)从下面来支撑的。在“呀呀儿语”之中,那些毫无关联的、自由浮动的、意义空洞的能指实际上完全受到了享乐的浸润。【55】这是拉康著作中的另一个根本性的转折,从而复杂化了拉康在1950年代发展出来的很多先前的对立。至此,便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领域,意义(sens)在其中受到了享乐的高涨所污染,拉康创造了一个新词“义爽”(joui-sens,该词可以翻译作“意义中的享乐”或是“意义的享乐”)来表示这一领域。享乐不再仅仅是一种“超越于”语言之外的力量;它同样是一种“内在于”语言之中的力量。
- 拜德雅重磅新书,欢迎至微店预订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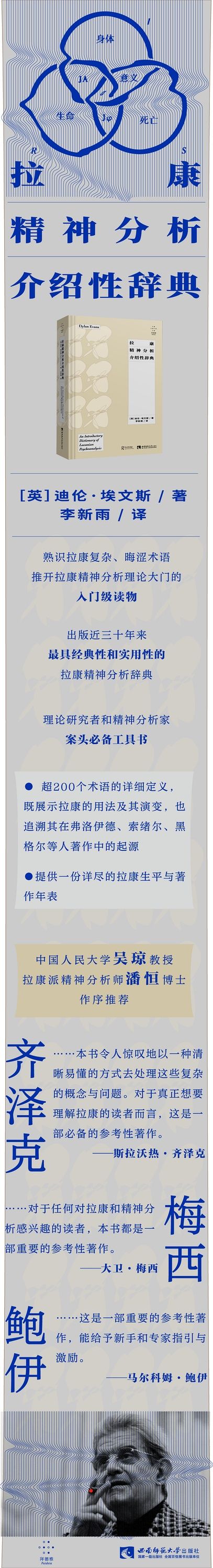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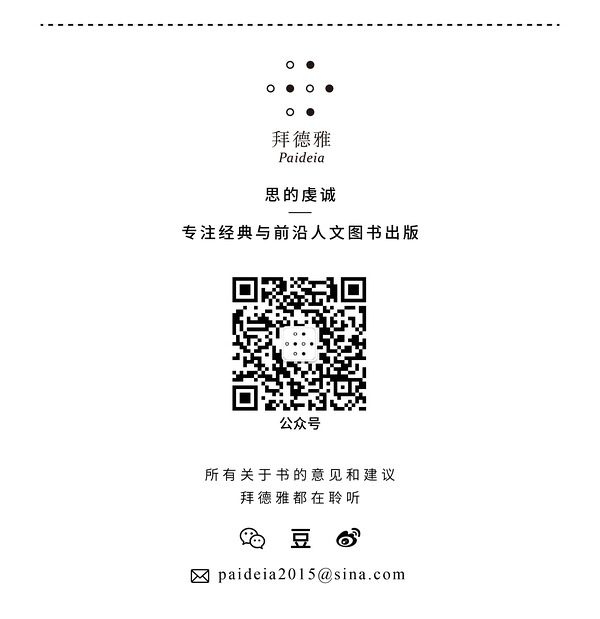
微店购书
相关知识
女人性高潮五大特点
1 亿女性深陷减肥焦虑?科轻乐携手哥伦比亚大学助力女性重塑曲线
欲望之火:欲望
快乐双语,魅力校园(48217)
揭秘 提高男女性欲的妙招
性高潮
【特别策划】夜跑=健身+快乐
关于音乐治疗与儿童心理健康
加拿大心理学家:保持自律并非如苦行僧克制欲望,越克制越易放弃
明星瘦身秘籍大揭秘:娱乐圈健康减肥风潮解析
网址: 拉康 / “享乐” → 快乐、高潮、欲望、伦理学、大他者、女性、身体、语言 https://m.trfsz.com/newsview541856.html